乌尔里希·茨温利
| 乌尔里希·茨温利 | |
|---|---|
 汉斯·阿斯佩尔1531年所绘的茨温利油画肖像 | |
| 出生 | 1484年1月1日 |
| 逝世 | 1531年10月11日(47岁) |
| 职业 | 牧师、神学家 |

乌尔里希·茨温利(德语:Ulrich Zwingli 或 Huldrych Zwingli,1484年1月1日—1531年10月11日),基督教新教神学家,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
茨温利生于瑞士维尔德豪斯。当时是瑞士爱国主义刚兴起的时候,瑞士佣兵制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茨温利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接受教育,深受人文主义影响。当他在格拉鲁斯与艾恩西德尔恩担任神父后,仍继续他的学业,受到伊拉斯谟著作的影响。茨温利本身反对教会传统、赎罪券和崇拜圣母玛丽亚等传统信仰。
1518年茨温利成为苏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在那里开始宣扬宗教改革的思想。1522年因为反对在大斋期的斋戒,公开吃香肠,开始受到公众关注。在著作中,他指出在教会阶级的腐败,提倡教士结婚,并攻击礼拜场所使用圣像。1525年,茨温利推出了新的礼仪。对于婴儿洗礼,茨温利曾与重洗派一起试图废除,但后来因政治因素妥协,导致与坚持进一步改革的重洗派决裂。因为茨温利与重洗派的冲突导致重洗派被迫害,历史学家曾争论他是否使苏黎世成为一个神权政治的城邦。[1]
之后宗教改革扩及瑞士邦联其他地区,但有些城邦仍倾向维持天主教,瑞士邦联因此依宗教分裂为支持宗教改革的城邦联盟,以及支持天主教的城邦联盟。1529年,战争尚未爆发。该年,茨温利与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的马尔堡会面协商,企图整合双方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歧。马尔堡会议中,前14条半都达成共识,但最后讨论圣餐礼时对圣餐意义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导致两派整合失败。马丁·路德认为圣餐中基督的确实质降临,是为同质说。而茨温利则认为圣餐只是一种纪念基督的象征,即象征说。
1531年,茨温利的联盟意图对天主教各城邦进行粮食封锁,于是有五个天主教城邦突袭苏黎世,茨温利以随军牧师的身份战死,年仅47岁。茨温利所留下的神学思想、礼仪还有教会制度,至今仍影响着许多新教教会,如重洗派。
历史背景
[编辑]
在茨温利时代的瑞士邦联包含13个城邦(自治州)、附属州和共同贵族领地。与现代在联邦政府下运作的瑞士联邦不同,13个城邦接近完全独立,进行自己的内政与外交,邦联内及邦联外的城邦形成各自的同盟。这种相对独立的状态是瑞士宗教改革时期冲突的原因,各州因此分为不同宗派的阵营。军事上的野心也加剧了进一步的竞争,以获得土地和资源,如同古苏黎世战争。[2]
15、16世纪间欧洲的政治环境也同样动荡不安。几个世纪以来,瑞士邦联的外交政策是由它与它的强邻—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名义上,邦联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然而,经过一连串的战争,士瓦本战争之后,邦联已经事实上独立。当时两个大陆强权、其他次强权(如米兰公国、萨伏依公国),以及教皇国正在互相竞争、对抗,对邦联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也就是此时,瑞士邦联的佣兵制度受到质疑。茨温利在辩论时,以宗教观点反对因城邦政府的财政因素,派出年轻的瑞士士兵参与外国的战争。[3]
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促成瑞士邦联国族主义的兴起,术语“祖国”(德语:patria)被使用,开始有超越各城邦之上的意义。在此同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普遍价值、对奖学金的重视都在此生根。包括被称为“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也多次来访,停留相当长的时间。茨温利正是诞生在这种瑞士爱国主义与人文主义交错的环境。[4]
生平
[编辑]早年(1484-1518年)
[编辑]
茨温利1484年1月1日出生于瑞士图根堡山谷中的维尔德豪斯,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第3个。他的父亲乌尔里希,在社区法警或首席地方法官的管理扮演主要角色。[5]茨温利的小学教育来自他在韦森当神父的叔叔巴塞洛缪,在那里他可能遇到了卡塔琳娜·冯·施文。[6]十岁时,茨温利被送往巴塞尔接受中学教育,在法官格雷戈里的指导下学会拉丁文。在巴塞尔的三年过后,他停留一小段时间在伯尔尼,接触人文主义学者亨利·沃尔夫林。伯尔尼的道明会试图说服茨温利加入他们的组织,或许是要收他为新手。[7]然而,由于父亲和叔叔反对,他没有完成他的拉丁文研究就离开伯尔尼。[8]1498年的冬季学期他进入维也纳大学,但似乎遭到开除。茨温利在1499年的活动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在1500年的夏季学期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在维也纳的研究。[9]1502年之后他前往巴塞尔大学,在15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10]
1506年9月29日,茨温利在康士坦兹被任命为当地教区的宗座,并在他的家乡维尔德豪斯庆祝他的第一场弥撒。做为一名年轻的神父,茨温利学过一些神学,不过这在当时并不会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他的第一个教会职务是格拉鲁斯镇的神父,在那里待了十年之久。就是在格拉鲁斯,许多的士兵都在欧洲当佣兵,茨温利也因此开始参与政治。当时瑞士邦联被卷入邻国(法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教皇国)之间许多的战事,茨温利选择站在罗马这一边。作为回报,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奖励茨温利,通过提供年度退休金给他。茨温利以随军神父的身份,参与了在意大利的几次战争,包括1513年诺瓦拉战役。然而,瑞士邦联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导致格拉鲁斯的立场开始从支持教皇国倒向法国。属于教皇党的茨温利因此处境尴尬,决定撤退到施维茨的艾因西德伦。这时的茨温利已经开始相信唯利是图的服事是不道德的,且对于未来的任何事,瑞士的团结是必须的。现存他最早的一些著作,例如《牛》(1510)和《迷宫》(1516),使用寓言和讽刺攻击佣兵制。他的同胞则是在法国、帝国和教皇三方夹缝中求生的正直人。[11]茨温利住在艾因西德伦的两年,完全退出政治,致力于教会活动和个人研究。[12][13]
茨温利在格拉鲁斯和艾因西德伦当神父的这段时间,特征是内在的成长与发展。他专精希腊文,并且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书库有超过300册,使他可以钻研古典学、教父学和经院哲学著作。他与瑞士的人文主义社群通信交流,并开始研究伊拉斯谟的著作。伊拉斯谟在1514年8月和1516年5月之间来到巴塞尔时,茨温利把握机会与他见面。茨温利转变为相对的和平主义,并且专注在宣教上,都与伊拉斯谟的影响有关。[14]
1518年末,苏黎世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职出缺,苏黎世大教堂认可茨温利是位杰出的宣教士与作家。他与人文主义的连结,是一些教会同情伊拉斯谟改革的关键因素。此外,他对法国和佣兵制的反对,也受到苏黎世政治家们的欢迎。1518年12月11日,苏黎世大教堂选出茨温利为“受薪神父”。12月27日,他搬到苏黎世,永久在此定居。[15][16]
苏黎世事工的开始(1519-1521年)
[编辑]
1519年1月1日,茨温利开始第一次在苏黎世的讲道。当时流行只在特定节日传讲福音,但茨温利使用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解经讲道,也就是所谓的持续读经法。[17]他每周日持续固定的进度解经,直到一卷书读完为止。马太福音之后是使徒行传、新约书信,然后开始旧约圣经。茨温利为何如此做的动机并不清楚,但他在讲道中试图实现道德和宗教的改进,目标与伊拉斯谟的改革相媲美。
1520年后的某个时段,茨温利的神学开始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形式,既不属于伊拉斯谟也不属于马丁路德。学界对于他独特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定论。[18]一种观点认为茨温利原先是个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然后马丁路德对他的神学转向有着关键性的影响。[19]另一种观点认为茨温利实际上没有太注意到路德的神学,所以仍属于人文主义改革运动的一部分。[20]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茨温利不是完全地追随伊拉斯谟,早在1516年他的神学就开始走向独自发展。[21]
茨温利的神学立场逐渐通过他的讲道表明。他抨击道德腐败,在这当中指名道姓地谴责那些人。教士则是被指责怠惰和生活优渥。1519年,茨温利明确拒绝敬奉圣人,并呼吁需要辨别真实和虚假的教导。他怀疑地狱,坚称未受洗礼的儿童不是该死的,并质疑逐教会绝罚的权力。他抨击宣称什一奉献是一个神圣机构的说法,而是具有最伟大的神学和社会影响。[22]这直接违背了教会的经济利益。一位在选举中支持茨温利的长老康拉德·霍夫曼,曾在信中抱怨他的讲道。教会中有一些人支持霍夫曼,但反对派势力并没有非常大。茨温利坚持他不是一个创新者,他讲道的唯一基础是圣经。[23][24]
在康斯坦茨教区内,伯纳迪恩桑森因对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贡献而获得大赦。桑森在1519年一月底抵达苏黎世,会友们希望茨温利对此提出质问。他因此不高兴地回应,人们没有被适当了地教导大赦的条件,导致一些人企图用自己的金钱来蒙混过关。这是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10月31日)后的隔年。[25]苏黎世议会拒绝桑森入境。由于罗马当局急于遏止路德所引起的风波,康斯坦茨主教否认对于桑森的任何支持,并且被召回。[26]
1519年8月,苏黎世爆发严重的黑死病疫情,造成至少1/4的人口死亡。所有有能力离开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茨温利依然继续坚守他的岗位。9月,他也染病,并且差点丧命。他写了一首预备死亡的诗,被称为茨温利的〈瘟疫诗〉(Zwingli's Pestlied),由三个部分组成:病情发作、贴近死亡和恢复的喜悦。诗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写到:“凭你意行,因我无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毁。”[27]
茨温利恢复之后的几年,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当苏黎世大教堂的委员会出现空缺时,茨温利在1521年4月29日获选递补空缺。成为教会委员后,他也成为苏黎世的完全公民,并继续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职。[28][29]
分歧的出现(1522年)
[编辑]第一次关于茨温利讲道的争议在1522年的大斋期爆发。第一个要禁食的星期日(3月9日),十多人邀请了茨温利,在克里斯多弗•福罗切尔住所举办“香肠晚餐”,他们切了两条熏香肠,故意违反禁食的规条。茨温利在4月16日的讲道公开解释此行为,主题是〈论食物的选择和自由〉(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 der Speisen )。他注意到关于大斋期的这些规条,在圣经中都找不到清晰的普遍原则,因此违犯这些规则并不是罪。这次事件,后来称作“香肠事件”,被认为是瑞士宗教改革的开始。[30]在这篇解释文发表之前,康斯坦茨教区马上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黎世。市议会投票的结果支持茨温利,谴责禁食的规条,但认定这属于宗教事务,要求宗教当局对此澄清。主教在5月24日回应苏黎世大教堂和市议会,重申传统的立场。[31]
这次事件后,7月2日,茨温利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朋友也向主教请愿,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应守独身的规条。两周后,大量印制的请愿书〈对同盟友好的请愿与训诫〉(Eine freundliche Bitte und Ermahnung an die Eidgenossen ),在德意志公开传递。这议题对茨温利而言不单是抽象的问题,同年早些时候,他已经秘密娶了一位寡妇 -安娜·赖因哈特。公共皆知道他们同居,不过他们公开的婚礼在1524年4月2日,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三个月前才举行。[32]他们最终有四个孩子: 蕾古拉、威廉、乌尔里希和安娜。当请愿书传到世俗政府,主教回应要求苏黎世政府应继续维持一贯的教会秩序。其他瑞士的神职人员参加了茨温利的诉求,并鼓励他写下他关于信仰的第一份重要声明〈最初与最后的话〉(Apologeticus Archeteles)。他为自己被控煽动叛乱和异端的罪名辩护。他认为由于教廷的腐败,他们并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地方教会事务。[33]
苏黎世纠纷(1523年)
[编辑]
1522年的事件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获得澄清,不仅苏黎世与主教之间的不安持续,苏黎世州与邦联内各伙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2月22日,国会建议其成员禁止新的教义,强烈的控诉直接针对苏黎世。市议会认为有必要主动出击,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一次辩论
[编辑]1523年1月,苏黎世市议会邀请了城市和偏乡地区的神职人员参与会议,使各派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也邀请了主教。市议会将对哪一种立场可以继续传扬做出决定。本次会议被称做是“第一次苏黎世辩论”,发生在1523年1月29日。[34][35]
本次会议吸引了大批群众,大约有600人参加。主教派他的副主教,约翰·法贝尔率领代表团参加。茨温利将他的立场总结在《六十七条》(Schlussreden)。[36][37]法布里没有料想到茨温利已经预备好要进行正式的学术辩论[38],他在外行人面前避谈神学,只是一再地强调坚持教会权柄的必要。市议会最终投票决定茨温利可以继续他的讲道,并且所有教士必须按照圣经教导。[39][40]
第二次辩论
[编辑]1523年9月,茨温利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父莱奥·尤德,公开呼吁破坏圣像,清除圣人雕像和其他圣像,导致示威和反传统运动。市议会决定在第二次辩论中处理圣像问题。弥撒的存在和它献祭的角色也被列为此次讨论的主题。弥撒的支持者声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献祭,而茨温利声称这是一个纪念。如同第一次论辩,市议会邀请了苏黎世的神职人员和康斯坦茨主教。然而这一次还额外邀请一些外人,库尔教区和巴塞尔教区、巴塞尔大学,还有瑞士邦联另外十二名成员也应邀参加。约九百人参加这次会议,但主教与教廷都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在1523年10月26日开始,历时两天。[41][42]
茨温利再次率先申论。他的对手是康拉德·霍夫曼,当初在教会选举支持茨温利的长老。参加者还有一群年轻人,要求更彻底更迅速的改革,主张以成人洗礼取代幼儿洗礼。该小组由重洗派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康拉德·格列伯领导。会议的前三天虽然对圣像和弥撒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但最终变成是在争论究竟是市议会还是教廷有权力决定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茨温利的追随者,阿尔高州的一位神父康拉德·施密德,提出一项务实的建议。由于目前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圣像毫无价值,施密德建议教士若宣讲此议题应受惩罚。他认为,人们的意见会逐渐改变,渐渐跟着自愿去除圣像。因此,施密德拒绝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反传统运动,但支持茨温利的立场。11月,市议会通过支持施密德的议案。茨温利写了一本小册子《基督教简介》(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讨论教士的福音责任。市议会将这本小册子送给神职人员和邦联的其他成员。[43][44]
苏黎世宗教改革的进展(1524-1525年)
[编辑]
在1523年12月,市议会设下了期限,要求在1524年的五旬节前解决废除弥撒和圣像的问题。茨温利对此给出了正式的意见〈关于圣像和弥撒的建议〉(Vorschlag wegen der Bilder und der Messe )。他没有主张立即、全面的取消。市议会决定渐进式的去除苏黎世的圣像,但农村教会被授权可以表决决定。废除弥撒一案则被推迟。[45]
宗教改革的果效开始出现在1524年年初。圣烛节没有被庆祝,长袍僧侣游行被取消,林登霍夫的棕枝主日礼拜没有棕榈枝和圣髑,祭坛后的三联画在大斋期过后仍然是覆盖的。[46]对改革的反对来自康拉德·霍夫曼和他的追随者,但市议会决定维持政府的授权。当霍夫曼离开了苏黎世,反对的主要力量从城邦内反改革的神父,变成是外在对宗教改革的打压。康斯坦茨主教试图干预维持弥撒和圣像崇拜,茨温利则撰写了市议会的官方回应,结果城市和教区断绝彼此之间所有关系。[47]
虽然市议会对于废除弥撒有过犹豫,传统礼仪行使的机会逐渐下降,仅允许牧师可以非正式地为要求者举行庆祝弥撒。由于个别牧师各自以他们认为合适的做法修改礼仪,茨温利被要求以德语设计一套圣餐礼仪来解决这一混乱的局面。这是发表在〈圣餐的行为与意义〉(Aktion oder Brauch des Nachtmahls)。复活节前不久,茨温利和他的亲信要求市议会取消弥撒并引进新的崇拜礼仪。在濯足节,1525年4月13日,茨温利在他新的礼拜仪式中举行圣餐。使用木杯子和盘子以避免流于外在的形式,会众坐在预备好的桌子上,为要强调圣餐为“餐”的面向。讲道是崇拜的中心,没有管风琴和诗歌。茨温利建议礼拜中讲道的重要性,认为圣餐举行的次数每年应该以四次为限。[48]
有一段时间茨温利指控虚伪的托钵修会,要求废除他们以支持真正的穷人。他建议改修道院为医院和福利机构,并纳入他们的财富为福利基金。这些通过重组苏黎世大教堂和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将剩余的修士和修女强制退休而完成。市议会将一些教会功能世俗化,并建立了新的穷人福利计划。茨温利请求在苏黎世大教堂里建立拉丁学校 -预言(卡罗莱纳)学校,获得市议会同意。1525年6月19日学校正式开幕,供神职人员培训和再进修,茨温利和里欧·杰为教师。苏黎世圣经译本,传统上归功于茨温利,并由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印刷,有着“预言学校”团队合作的标志。[49]学界从外部和文体的证据,仍未完全了解茨温利参与程度。[50][51]
与重洗派的冲突(1525-1527年)
[编辑]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之后,许多宗教改革的激进派认为茨温利对苏黎世议会让步太多。他们拒绝市民政府的角色,并要求立即建立信众的教会。康拉德·格列伯,激进派与新兴重洗派的领袖,私下谈论到茨温利时显得相当轻蔑。1524年8月15日,市议会坚持所有的新生儿都要受幼儿洗礼。茨温利秘密地跟格列伯的小组协商后,1524年底,市议会呼吁召开正式的讨论会。当会谈中断,茨温利发表〈谁导致动乱〉(Wer Ursache gebe zu Aufruhr),陈明反对的观点。[52]公开辩论在1525年1月17日举行,市议会赞同茨温利的决定。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受幼儿洗礼的人们被要求离开苏黎世。激进派忽视这一措施,在1月21日,他们在另一位激进派领导人费利克斯·曼茨的母亲的房子聚集。在那里格列伯和第三领导者乔治·布老若克,进行了有纪录的第一次重洗派成人洗礼。[53]
2月2日,市议会再次要求所有婴儿应该接受洗礼,不遵守的人将被逮捕与受罚,包括曼茨和布老若克。茨温利和里欧·杰前往探访他们,市议会则是举行了更多公开辩论。同时,新的教导散布到瑞士邦联其他区域,以及一些士瓦本的城镇。11月6-8日,关于洗礼的最后一次辩论在苏黎世大教堂举行。格列伯、曼茨、布老若克在茨温利、杰,和其他改革者面前为他们自己的主张辩护。他们的观点彼此间并没有交集,双方都坚持原本的立场,辩论演变成一片吵杂,双方互相谩骂。[54]
苏黎世市议会最终决定完全不妥协,在1526年3月7日发布了恶名昭彰的命令,任何重洗的人将处死。[55]虽然技术上来说茨温利没有参与这项决定,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反对。曾经发誓离开苏黎世并不再施行洗礼的费利克斯·曼茨,故意回来继续进行重洗派的活动。他被逮捕和审判之后,1527年1月5日在利马特河被以溺刑处死。他是第一位重洗派的殉道者,接着还有其他三位被处死。之后其他重洗派逃离或被驱逐出苏黎世。[56][57]
瑞士邦联的宗教改革(1526–1528年)
[编辑]
1524年4月,卢塞恩、乌里、施维茨、下瓦尔登和楚格等五个州形成“五国联盟”(die fünf Orte),以对抗茨温利的改革。他们联系了马丁·路德的对手约翰·埃克,曾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和路德辩论。埃克要求举行辩论,他和茨温利都接受。然而,他们不能同意评审机关的选择、辩论的位置,还有使用瑞士国会做为法庭。由于无法达成共识,茨温利决定抵制这次辩论。1526年5月19日,各州都派出代表前往巴登。尽管苏黎世的代表有出席,但他们没有参加议程。埃克领导天主教一方,而改革者由巴塞尔的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领导。厄科兰帕迪乌斯是符腾堡的神学家,曾与茨温利有广泛而友好的信件往来。随着辩论的进行,茨温利持续接受会议的资讯,并印小册子表达他的意见。不过这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国会决定反对茨温利。他被禁止,不得再发送他的著作。邦联十三个成员中,格拉鲁斯、索洛图恩、弗里堡、阿彭策尔以及五国联盟投票反对茨温利。伯尔尼、巴塞尔、沙夫豪森和苏黎世支持他。[58]
巴登辩论暴露出邦联内部在宗教问题上的深深裂痕。宗教改革已经开始出现在其他州。邦联的附属州圣加仑市,由改革市派长约阿希姆·瓦迪安带领,在苏黎世两年之后的1527年废止了弥撒。在巴塞尔,虽然茨温利曾与厄科兰帕迪乌斯有密切的关系,但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革的裁决,直到1529年4月1日废止弥撒。沙夫豪森则是一直密切关注苏黎世做为典范,在1529年9月正式通过的改革。
伯尔尼的情况,伯尔尼大教堂的神父德迈·哈勒和诗人画家兼政治家尼克劳斯·曼努埃尔,为了改革而参加竞选。不过伯尔尼是否是一个支持改革的州,要到另一场辩论之后才确立。伯尔尼辩论有450人参加,包括伯尔尼和其他州的神父,还有邦联之外的一些神学家,如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马丁·比塞和沃尔夫冈·卡皮托、来自康斯坦茨的安布罗修斯·布拉雷尔、来自纽伦堡的安德烈亚斯·阿尔特哈默。埃克和约翰·法贝尔拒绝出席,支持天主教的各州也没有派出代表。会议从1528年1月6日开始,持续近三个星期。茨温利承担捍卫改革的主要责任,在明斯特有过两次的演讲。1528年2月7日,议会下令宗教改革正式在伯尔尼建立。[59]
第一次卡珀尔战争(1529年)
[编辑]
早在伯尔尼辩论之前,茨温利就试图建立一个改革派城邦的联盟。当伯尔尼正式接受改革,“基督教公民联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便宣告成立。[60]联盟的第一场会议于1528年1月5~6日在伯尔尼,与康斯坦茨和苏黎世的代表共同举行。其他城市,包括巴塞尔、比尔、米卢斯、沙夫豪森和圣加仑随后加入该联盟。“五国同盟”(天主教)感受到包围和孤立,开始寻求更多外部的盟友。2个月的协商后,“五国同盟”与奥地利的斐迪南在1529年4月组成“基督教联盟”(die Christliche Vereinigung)。[61][62]
对奥条约签订后不久,改革派的传教士雅各·布凯泽,在乌茨纳赫被逮捕,在施维茨被处决。此事引发茨温利激烈反应。他起草了〈关于战争的建议〉(Ratschlag über den Krieg )给予政府,概述了对天主教国家发动攻击还有实行其他措施的理由。在苏黎世将要展开行动时,从伯尔尼的一个代表团(包括尼古拉斯·曼努埃尔)抵达苏黎世,劝苏黎世以和平方式解决此事。曼努埃尔指出,发动攻击会使伯尔尼暴露在进一步的危险中,尤其在与天主教瓦莱和萨伏依公国接壤的南翼。他曾说:“长矛和刀剑无法带来信心。”[63]但是苏黎世知道伯尔尼不得不默许,决定要独自行动。1529年6月8日苏黎世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并且宣战。“五国同盟”则被奥地利放弃,部队规模可能只有9千人。双方部队在卡珀尔附近遭遇,但因为茨温利的亲戚汉斯·艾伯利介入,双方休战。[64][65]
茨温利不得不提出停战条款。他要求“基督教联盟”必须解散;改革派的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天主教国家;禁止养老保险制度;支付战争赔款;赔偿殉道者雅各·凯泽的孩子。曼努埃尔参与了谈判。伯尔尼没有打算坚持自由宣教权和禁止养老保险制度。苏黎世和伯尔尼不能接受“五国同盟”(天主教)仅答应解散与奥地利的结盟。茨温利大失所望,这也标志着他政治声望的下降。[66]卡珀尔的第一个土地和平令(der erste Landfriede)生效,战争在6月24日结束。[67]
马尔堡会谈(1529年)
[编辑]- 参见:马尔堡会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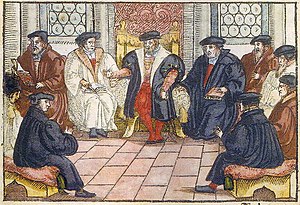
当茨温利在瑞士邦联展开宗教改革的政治工作时,他与他的同事们发展了他的神学观点。马丁路德与茨温利之间最著名的分歧就是关于圣餐意义的解释。这个分歧起源时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前同事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他发行了三本关于圣餐的小册子,反对圣餐当中基督真实临在的解释。这些小册子于1524年在巴塞尔发表,得到厄科兰帕迪乌斯和茨温利的认可。路德拒绝卡尔施塔特的论点,认为茨温利也是与卡尔施塔特一伙的。茨温利开始透过一些出版品表达他对圣餐的想法,包括《论圣餐》(de Eucharistia)。 他攻击真实临在的观点,认为耶稣的祝圣祷文中“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象征意义。[68]因此,茨温利声称圣餐中没有基督真实的临在,将这段经文理解为一种隐喻。实际上,这餐是象征最后的晚餐。[69]
1527年春,路德在〈基督的这些话‘这是我的身体’等等-仍然坚决抵制这些狂热者〉(Dass Diese Worte Christi "Das ist mein Leib etc." noch fest stehen wider die Schwarmgeister)中强烈反对茨温利的意见。争论一直持续到1528年,马丁·布策试图搭建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桥梁。当时黑森的菲利普想要建立统合所有新教势力的政治同盟,邀请双方前来马尔堡讨论彼此间的分歧。此事件被称为马尔堡会谈。[70]
茨温利接受了菲利普的邀请,他自信能说服路德。相较之下,路德没想到要出来会谈,在菲利普的敦促下才不得不参加。1529年9月28日,茨温利在厄科兰帕迪乌斯的陪同下抵达,路德和菲利普·梅兰希通随后不久也到。其他神学家也有参加,包括马丁·布策、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约翰内斯·布伦茨、贾斯特斯·乔纳斯。[71]辩论在10月1到3日举行,结果发表为〈马尔堡十五条〉。参与者仅能同意前十四条,但第十五条关于基督圣餐的解释仍然意见分歧。此后,每边宣称他们是胜利者,但实际上争议并没有解决,最终导致两个不同的新教教派各自发展。[72]
政治的变化与第二次卡珀尔战争(1529-1531年)
[编辑]- 参见:第二次卡珀尔战争


随着马尔堡会谈的失败和邦联的分裂,茨温利将他的目标转向与黑森的伯爵菲利普一世同盟。他与菲利普维持积极的联络。虽然伯尔尼拒绝参加,但经过漫长的努力后,苏黎世、巴赛尔、斯特拉斯堡与菲利普在1530年11月签定共同防御条约。茨温利也亲自与法国的外交代表交涉,但双方差距甚大。法国希望与“五国同盟”(天主教)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威尼斯和米兰的尝试也失败了。[73]
当茨温利在为组织政治联盟努力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要裁决信仰问题,邀请新教徒前往奥格斯堡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此路德派提出了《奥格斯堡信条》。另外在马丁·布策的领导下,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林道等几个城市产生了《四城信条》,采取了介于马丁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中间立场。不过属于茨温利领导“基督教市民同盟”的城邦(Burgrecht cities)来不及形成他们自己的信条。由茨温利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告白《信心与理性》(Fidei ratio),以使徒信经为基础的十二篇文章,强烈抨击天主教和路德宗。路德宗对此私下批评,没有公开回应。茨温利和路德的老对手约翰·埃克,则是出书反驳茨温利,并提交给皇帝。[74]
1530年年末黑森的菲利普一世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四城信条》的四个城邦加入了以路德宗《奥格斯堡信条》为主的同盟。由于联盟的条件宽松,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原本考虑加入。但茨温利的信仰无法接受《四城信条》,并写信严厉拒绝了布策尔和卡皮托。这侵犯到菲利普一世的立场,使他切断茨温利与联盟的关系。导致“市民同盟”在瑞士邦联的宗教冲突中失去任何外部的盟友。[75]
第一次卡珀尔的和平条约中没有保障新教在天主教国家传教的权利。茨温利认为这样表示是允许的,但五国同盟完全拒绝。“市民联盟”考虑以不同的方式对“五国同盟”施加压力,巴塞尔和沙夫豪森认为应该以外交手段为主,而苏黎世想以军事手段解决。茨温利和里欧·杰都主张对“五国同盟”发动攻击。伯尔尼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最终获得了支持。1531年5月,苏黎世勉强同意对“五国同盟”实行粮食封锁。但到了10月,封锁的效果仍然有限,伯尔尼决定撤销封锁,苏黎世则希望维持封锁,“市民联盟”内部对此争论不休。[76]
1531年10月9日,“五国同盟”决定先下手为强,对苏黎世宣战。苏黎世由于内部纷争动员缓慢。10月11日,苏黎世布署在卡珀尔附近部队(3500人)遭遇到“五国同盟”两倍的部队进攻。包括茨温利在内许多牧师都上了前线,战斗持续不到一小时,茨温利是苏黎世军队阵亡的500人之一。[77]
茨温利曾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属于基督的;第二是他所捍卫的国家瑞士邦联;第三是他生活了12年的城市苏黎世。讽刺的是,他在47岁去世时,不是为了基督,也不是为了瑞士邦联,而是为了苏黎世。[78]对此马丁路德写到:“幸好茨温利、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和康拉德·佩利坎都死在战场上,否则我们不可能维持与黑森的菲利普一世、斯特拉斯堡和其他我们的邻邦的关系。哦!这是个胜利,他们灭亡了。上帝的旨意何其好。”卡尔施塔特和佩利根的死讯是当时误传。厄科兰帕迪乌斯则是在11月24日去世。伊拉斯谟写到:“对于两位宣教士,茨温利和厄科兰帕迪乌斯的死讯,我们从巨大的恐惧中释怀,他们的生命让许多心灵产生难以置信的变化。这是至高神奇妙的作为。”此外伊拉斯谟也写到:“如果贝罗纳(古罗马战争女神)青睐他们,那么这一切也可能临到我们之上。”[79]
大事记
[编辑]- 1484年(出生)元旦生于瑞士,家境富裕,受良好的人文教育。
- 1498年(14岁)进入维也纳大学,后转巴塞尔大学,1504年(20岁)毕业。
- 1499年 (15岁) 瑞士邦联独立,但经济贫困,佣兵盛行。茨温利之后因反对佣兵制度而涉入政治。
- 1506年(22岁)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
- 1516年(32岁)遇见伊拉斯谟,并成为伊拉斯谟的忠实门徒。
- 1519年(35岁)元旦,担任苏黎世大教堂教会之神父。
- 1519年 (35岁) 接触马丁路德的一些著作,影响茨温利一些早期的论述。
- 1519年 (35岁) 因探视病患而染上黑死病,几乎丧命。他哀求上帝医治,并奉献一生事主。在这过程中,强化了他宗教结合社会改革的决心。
- 1522年(38岁)与寡妇安娜秘密结婚。
- 1523年(39岁)主持苏黎世议会的教义辩论。发表《六十七条》。
- 1523年(39岁)10月举行第二次辩论。与会者多数赞成废除弥撒。
- 1529年(45岁)前往马尔堡与马丁·路德讨论教会体制,但会谈最后因对圣餐意义的歧异而破裂。
- 1531年(47岁)10月11日在卡佩尔战役中受伤,最后被敌人用石头打死。
与天主教的主要冲突
[编辑]- 1522年罗马天主教高举传统与圣经相等,慈运理断然拒绝此项宣告。他并于同年八月出版《始与终》,坚持圣经为唯一之权威,并认为圣经是人人可读的。
- 1523年拟定《六十七条》(Schlussreden),攻击教皇、圣徒崇拜、善功、禁食、节期、朝圣、修道会、教牧独身、告解、赎罪券、苦行、炼狱等等。
- 1523年起多次公开辩论,废弥撒、除圣像、毁管风琴等。
- 与瑞士邦联中罗马天主教势力城邦的战争。[80]
神学思想
[编辑]上帝有至高的主权
[编辑]- 上帝的主权——有关上帝的教理,是茨温利神学体系的中心。他的神学架构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在茨温利的作品《论神的照管》一书中,茨温利想要从自然神学开始,来证实神的存在和本性乃是决定一切的实有,并且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祂的至高主权同时掌管着自然界一切的定律与历史进程中一切事件的发生与演变 [81]。若上帝“想要”改变一切的常态,以致于脱离一切理性中的常轨,仍然是神自己的权力。凡是违背神旨意的事都不会发生,因此茨温利认为一切的邪恶和一切的良善,都一样可归因于上帝;连亚当犯罪堕落的事亦可归因于上帝。但我们不能据此控告上帝为有罪,因祂不处在律法之下。举凡偷盗、凶杀等罪行是人滥用“自由意志”而导致的行为,故人要受律法的定罪 [82]。上帝虽造了会堕落的人类,但祂也决定祂的独生子取了人性,以拯救堕落的人类。关于人的得救,茨温利强调“神恩独作说” [83]。
- 上帝的拣选与预定——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不变的、且是永恒的。蒙拣选者必然得救,即使这人尚未获得信心之前就死了。茨温利认为上帝的拣选不独在基督教之内,上帝的拣选能延伸到旧约的众圣徒,甚至也可以延伸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英雄和圣贤哲士。关于一个人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预定的。茨温利认为上帝的拣选与预定,乃是祂预知的原因 [83]。上帝的拣选只是指著预定得救者,以及他们将来在天上所要接受的命运而言;至于其余未被拣选的人,他们不仅自由任意地选择诅咒,他们也预定要承受下地狱的命运 [82]。
- 上帝给人活出信仰的力量——茨温利彻底的强调造物主与被造者的分际,双方必须分开而不可互相混乱。他也借此彻底除去教会内外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风气,例如宗教图像、政治领袖等。他更进一步追求上帝主权在信徒外在生活的彰显,他所努力的是,“内圣”的信仰体验必须达到“外王”的生活实践 [84]。
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编辑]- 圣经高于一切权威——茨温利非常强调圣经的原则,认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和传统及习俗中的最高权威,并且一切从人而来的传统,当然包括教会和教延中所流传的传统,都必须接受圣经的评判 [85]。基督教的神学应该要回归圣经并奠基于圣经,“惟靠圣经”是宗教改革家的口号与信念,一切无法在圣经中找到根据的传统或信仰,都应该被摒弃,或是被宣布无效,例如“马利亚无罪”的教义 [86]、以及茨温利在《六十七条》中用来攻击教皇、圣徒崇拜、善功、禁食、节期、朝圣、修道会、教牧独身、告解、赎罪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炼狱等等不合圣经的教导都是。而紧接着的是解经式的讲道、圣经书卷的注释、以及圣经神学方面著述的蓬勃发展 [87]。
-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有别于马丁·路德将圣经中的某些书卷高抬于其他书卷之上[来源请求],或质疑某些书卷的属灵价值[来源请求]。茨温利则一视同仁的将圣经中的各书卷都视为“神的道”,也认为都具有同样崇高的地位。茨温利在他牧会的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无视于罗马天主教的“统一进度”规范,坚持逐章逐节的在讲台上将全本新约圣经讲解清楚 [88],在当时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圣经,并且多以灵意解经的背景之下,茨温利他以文法字义的解经法,并以解经为中心的讲章,且连结在生活上的应用,此作风在当时独树一格。
- 圣经为信仰与生活中的最高准则——茨温利他不刻意去分辨律法与福音之间有何差别,他从律法的观点来运用圣经,并将圣经看成是一本生活的准则。在茨温利的想法中,律法就如同福音一般,都是上帝慈爱的启示,要叫人远离罪,并与上帝和好且保持亲密的关系。茨温利的主张是“凡圣经没有说的就不要去做” [89]。
圣礼为见证与纪念
[编辑]- 圣礼——茨温利认为“圣礼”的仪式并不能使人得着信心或恩典,这些恩赐乃是由圣灵所给予的,他更进一步以“礼仪”来替代“圣礼”这个词。茨温利认为圣礼只不过是一种“象征”的仪式,而非真正恩典的媒介 [90]。他认为圣礼使教会确信这个人具有信心,远大于圣礼使这人确信他是真有信心,真信心需要仪式来证明它的真实,并且是经得起考验的。圣礼实质上的功用,是为了教会而存在,并且为了宣扬和纪念基督的拯救行动以及这行动对个人的功效。圣礼也可以帮助人想到福音,并帮助我们记住基督的工作和表明我们的信心。茨温利也强调,在整个圣礼进行的过程中,圣灵是实际临在当中,并且接受礼仪者的信心。他坚持没有信心、拯救的恩典与赦免与这礼仪结合在一起 [87]。
- 浸礼——茨温利将“浸礼”等同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割礼”,只是在新约时代要成为神子民的一种入会仪式,也是表示神拣选的一个记号。茨温利并强烈否认重洗派“重洗”的必要性 [91]。
- 圣餐——茨温利的圣餐观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反对任何的迷信与传奇色彩,较为注重灵性与精神层面。同样的,茨温利强调圣餐也是一种纪念、象征性的行动 [92],他认为基督并未真实的临到圣餐的饼和酒里面,主餐只是一个纪念主的仪式,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因此纪念和宣扬基督的死。在主餐的仪式中,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清楚的表明自己是基督身体的一分子,彼此互为肢体 [93]。在圣餐上的歧见,成了马丁·路德与茨温利在马尔堡讨论教会体制的过程中,两者决裂的最主要原因,也造成了茨温利后来必须独自面对反对势力的困境。
影响
[编辑]
在沃木斯有一座茨温利的纪念雕像,一手持圣经,一手持刀剑,这代表他一生持守基督信仰,并且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全然摆上而不遗余力 [94]。茨温利一生都是个行动派,将他的理念实践出来,与当时的多方势力如罗马天主教、瑞士邦联政府议会、重洗派、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势力,都有过微妙的互动或激烈的交锋。甚至在他“政教合一”的理想中,亦曾联络一位德意志公爵,利用法国国王为后盾,并联合威尼斯舰队,想要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然而在他四十七岁时任随军神甫时,在战场上为敌人所杀。他的神学思想虽未臻完美、政教改革虽未竟全功,但他所留下的宝贵资产,提供后继的思想家与喀尔文一个改革的方向。
重要著作
[编辑]- 《始与终》(1522年)-坚持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并认为人人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
- 《六十七条》(1523年)-攻击教皇、圣徒崇拜、善功、禁食、节期、朝圣、修道会、教牧独身、告解、赎罪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炼狱等等不合圣经的教导。
- 《真假宗教诠释》(1525年)-详细说明宗教改革的理念及目的,并驳斥当时教会的败坏与谬误。此作品通常被视为第一本改革宗信条。
- 《论茨温利的信仰》(1530年)-茨温利陈述他对浸礼的观点。
- 《论神的照管》(1531年)-慈运理从自然神学开始,想要证实神的存在和本性乃是决定一切的实有,高高在上,同时决定自然与历史。
- 《基督教信仰浅释》(1531年)
参考文献
[编辑]- ^ Robert Walton, Zwingli's Theocracy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Gäbler 1986,第1–4页
- ^ Gäbler 1986,第4–6页
- ^ Gäbler 1986,第6–7页
- ^ Potter 1976,第6页
- ^ Katharina von Zimmern. frauen-und-reformation.de. [2014-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31).
- ^ Gäbler 1986,第24页; Potter 1976,第9页. Potter mentions this possibility. Gäbler states that Zwingli did not refute later claims by opponents that he had been a monk in Bern.
- ^ Gäbler 1986,第24页; Potter 1976,第9页
- ^ Gäbler 1986,第25页. The word exclusus (expelled) was added to his matriculation entry. Gäbler notes that without a date and reason, it does not conform to what was customary at the time.
- ^ Gäbler 1986,第26页
- ^ Stephens 1986,第8页; Potter 1976,第35, 37页
- ^ Gäbler 1986,第29–33页
- ^ Potter 1976,第22–40页
- ^ Gäbler 1986,第33–41页
- ^ Gäbler 1986,第43–44页
- ^ Potter 1976,第45–46页
- ^ Old 1998,第46–47页
- ^ Gäbler 1986,第44–45页
- ^ Gäbler 1986,第46页. Proponents of this view are Oskar Farner and Walther Köhler.
- ^ Gäbler 1986,第46页. Proponents of this view are Arthur Rich and Cornelius Augustijn.
- ^ Gäbler 1986,第46–47页. A proponent of this view is Gottfried W. Locher.
- ^ Gäbler 1986,第50页
- ^ Gäbler 1986,第49–52页
- ^ Potter 1976,第66页
- ^ Bainton 1995,第XII页
- ^ Potter 1976,第44, 66–67页
- ^ see e.g. Potter 1976,第69–70页
- ^ Gäbler 1986,第51页
- ^ Potter 1976,第73页
- ^ Denis Janz. A Reformation reader: primary texts with introductions. Fortress Press. 2008: 183 [2012-01-15]. ISBN 978-0-8006-6310-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7).
- ^ Gäbler 1986,第52–56页
- ^ Potter 1976,第80页
- ^ Gäbler 1986,第57–59页
- ^ Gäbler 1986,第63–65页
- ^ Potter 1976,第97–100页
- ^ Potter 1976,第99页
- ^ The Sixty-seven Articles are contained in Selected Works of Huldreich Zwingli, Philadelphia, 1901, pp. 111–117. At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13 March 2015.
- ^ Cameron 1991,第108页
- ^ Gäbler 1986,第67–71页
- ^ Potter 1976,第100–104页
- ^ Gäbler 1986,第72, 76–77页
- ^ Potter 1976,第130–131页
- ^ Gäbler 1986,第78–81页
- ^ Potter 1976,第131–135页
- ^ Gäbler 1986,第81–82页
- ^ Potter 1976,第138页
- ^ Gäbler 1986,第82–83页
- ^ Gäbler 1986,第105–106页
- ^ 根据Gäbler 1986,第102页,首部新旧约全书印成于1531年。其他来源也说是1529年或1530年。参见Estep 1986,第96页和Greenslade 1975,第106页。早期版本被称为弗罗绍尔圣经,参见Chadwick 2001,第35页。
- ^ Potter 1976,第222–223页
- ^ Gäbler 1986,第97–103页
- ^ Gäbler 1986,第125–126页
- ^ Potter 1976,第177–182页
- ^ Potter 1976,第183–186页
- ^ Potter 1976,第187页
- ^ Potter 1976,第186–188页
- ^ Sharp, John.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Anabaptists: Steps to Reconciliation, 26 June, 2004, Zurich, Switzerland. Mennonite Historical Committee. July 2004 [2012-12-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24). The descendants of the Zwinglian Reformation, the Reformed Church of Zurich,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abaptist movement (Amish, Hutterites, and Mennonites) held a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 at the Grossmünster on 26 June 2004. This link includes the conference program, and all statements made at that conference.
- ^ Gäbler 1986,第111–113页
- ^ Gäbler 1986,第113–119页
- ^ Locher 1981,第109页. Potter also translates Burgrecht as "Civic Union", while Gäbler 1986,第119页 translates it as "Fortress Law".
- ^ Gäbler 1986,第119–120页
- ^ Potter 1976,第352–355页
- ^ Potter 1976,第364页. In Early Modern German, "Warlich man mag mit spiess und halberten den glouben nit ingeben."
- ^ Gäbler 1986,第120–121页
- ^ Potter 1976,第362–367页
- ^ Potter 1976,第367–369页
- ^ Potter 1976,第371页
- ^ Potter 1976,第157页
- ^ Gäbler 1986,第131–135页
- ^ Gäbler 1986,第135–136页
- ^ Bainton 1995,第251页
- ^ Gäbler 1986,第136–138页
- ^ Gäbler 1986,第141–143页
- ^ Gäbler 1986,第143–146页
- ^ Gäbler 1986,第148页
- ^ Gäbler 1986,第148–150页
- ^ Gäbler 1986,第150–152页
- ^ Potter 1976,第414页
- ^ Philip Hughes (1957),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1960 reprint, Garden City, NY: Image Books, Ch. 4, "Luther. The First Protestants", Sec. v, "Zwingli", p. 139.
- ^ 张之宜著,《历代神学家偶摭》(台北:弘智出版社,1984),页204。
- ^ 奥尔森著,《神学的故事》,吴瑞诚等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页481。
- ^ 82.0 82.1 同上,页482。
- ^ 83.0 83.1 同上,页481。
- ^ 林鸿信着,《教理史下》(台北:礼记出版社,1996),页154-55。
- ^ 奥尔森著,《神学的故事》,吴瑞诚等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页479。
- ^ 麦葛福着,《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等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页85。
- ^ 87.0 87.1 同上。
- ^ 张之宜著,《历代神学家偶摭》(台北:弘智出版社,1984),页203。
- ^ 林鸿信着,《教理史下》(台北:礼记出版社,1996),页156。
- ^ 奥尔森著,《神学的故事》,吴瑞诚等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页483。
- ^ 同上,页484。
- ^ 林鸿信着,《教理史下》(台北:礼记出版社,1996),页159。
- ^ 奥尔森著,《神学的故事》,吴瑞诚等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页485。
- ^ 张之宜著,《历代神学家偶摭》(台北:弘智出版社,1984),页206。
参考书目
[编辑]- 林鸿信。《教理史下》。台北:礼记出版社,1996。
- 张之宜。《历代神学家偶摭》。台北:弘智出版社,1984。
- 麦葛福。《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等译。台北:校园出版社,1998。
- 奥尔森。《神学的故事》。吴瑞诚等译。台北:校园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