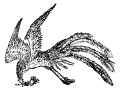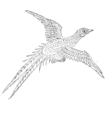山海经
| 山海经 | |
|---|---|
 | |
| 作者 | 不详 托名:大禹、伯益 |
| 编者 | 刘向 |
| 语言 | 中文 文字:上古汉语 |
| 成书年代 | 战国至秦汉 |
| 山海经 |
|---|
 |
| 山经 |
| 中山经 |
| 海经 |
|
海外南经 海外西经 海外北经 海外东经 海内南经 海内西经 海内北经 海内东经 大荒东经 大荒南经 大荒西经 大荒北经 海内经 |
《山海经》,先秦时期的古籍,作者不详,是一部载有怪奇悠谬之说、荟萃珍奇博物的神话地理志[1]。在古代的四部分类法中,或视为山川地志(史部地理类),或视为博物之书(子部小说类)[2]。随著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传入,对《山海经》的认识也突破了过往的框架。文学家鲁迅视之为古代的“巫书”,因其中记载上古巫师祭神厌鬼的方术仪典;神话学学者将其当作远古的神话,寄托了华夏先民奇幻瑰丽的想像[3]。一般认为该书涉及了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及民族各个方面的内容[4]。
《山海经》记载许多民间传说的妖怪,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传说,长期被认为是一部志怪之书[5],有人认定本书所记之事,荒诞不经不可轻信,但也有人肯定其价值,用以考证奇物异俗,山川形势[6]。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的探勘纪录,其中包括一些远古氏族谱系,祭祀神名,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2]。
《山海经》本有图画,其文字可能就是依图画内容而叙述出来[6][7]。不过,古图已亡佚不存,南朝张僧繇绘制、宋代舒雅重绘的10卷本242幅《山海经图》也没有流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山海经图本,来自于明朝的胡文焕本、蒋应镐本这两种[8]。
山海经现行本共18篇,3万馀字,是晋朝郭璞所注的本子,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1篇[6]。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和吴承志等人是本书重要的注解者[9]。
作者
[编辑]已知最早记载山海经一词的文献,是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赞:“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司马迁未提及作者是谁[6](汉书、论衡引史记此段文字时只提到“山经”)。
按刘歆〈上山海经表〉的说法,《山海经》出自唐虞之际,是大禹、伯益由治理洪水的缘故,至九州各处“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又纪“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以辨别九州土地的肥瘠,制定所要缴纳的田赋,区别事物之善恶,以利器用[10][11]。
然而,山海经中出现郡县名,又有夏禹以后史事,因此历代以来,有人怀疑其中有后人添加的文字,或完全否定为禹、益所作[6]。《周礼》疏中有“古山海经邹(邹衍)书”的说法[12]。朱熹、胡应麟等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是战国好奇之士所做。清朝学者毕沅主张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长久累积而成的集体成果。〈五臧山经〉的材料大概可远溯于夏代,但《山海经》之成书,时间大约是从战国晚期到汉代之间,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13],其中许多可能来自于口头传说[4]。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经〉作者是洛邑人。据蒙文通考证,《山海经》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萧兵推测此书可能是东方早期方士根据云集于燕齐的各国人士编纂整理而成。多数学者则认为写定《山海经》的是楚人,例如袁珂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表示:“《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过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13]。
《山海经》由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十八篇。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及注释者还有明朝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清朝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等。民国以后,则以神话学者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最为出名。
内容
[编辑]
文字
[编辑]《山海经》全书18篇,其中“山经”5篇,“海经”8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一篇,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信息。《山海经》中对于动物的记载,据统计有277种之多,有虎、豹、狕、熊、罴、狼、犬、兔、猪、马、猴、猿、猩、犀、牛、彘、鹿、麂、类、豚、禺、羚、羊、象、蛇、蝼、猥、訾、驼、獭、狐、糜、麈等,还有猼𫍙、毕方、帝江、何罗鱼、鸟和狌狌。郭璞认为狌狌就是猩猩。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经》中保存大量祭祀神祇的祭礼,原本都与《周礼》所载纪录对照研究,现在才发现可与新出土的战国简帛《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的祭祷纪录对比研究。
《山海经》记载了许多古代中国神话,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这种南西北东的顺序与后代从东开始,东南西北的顺序习惯不同,据研究与古代帝王座北朝南以及天南地北的空间观念有关。
《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视为数术略形法家,“形法”为一种依照外表判断事物好坏或命运的吉凶之术,如面相、手相、风水等等。可能是因为山海经列举出五方山川、四海邦国的怪物、风俗,能据此趋吉避凶,所以认定作一种数术。
古代中国也把《山海经》作地理书看待,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引用《山海经》的经文来注释《水经》,《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14]。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山海经》一书首次被列入“古史”类,与《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等书并入一类[2]。
不过,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所记事物难以求证,又多奇怪神异之处,故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明人胡应麟见其书“无论其事及其文,与典谟、《禹贡》迥不类也”,“怪诞之词,圣人所不道”,不相信其为地理书,而谓之为“古今语怪之祖”。清人修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耳。”将《山海经》归为子部小说类。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民间的街谈巷语、奇闻异事、笔记琐闻、稗官野史,属于诸子百家中的小说家[9]。
当代学者研究《山海经》趋向多元,不仅视《山海经》为文学想像的神话,亦重视其包含有上古信史的一面[9]。
山海图
[编辑]古山海经有图,郭璞作有《山海经图赞》,把他所见到的山海经图称作“畏兽画”。陶渊明所作诗文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山海经古图已亡佚不存,六朝张僧繇绘制、宋代舒雅重绘的10卷本242幅《山海经图》也没有流传下来[8]。
明清时代的文人对于山海图为何提出多种讨论。杨慎认为“九鼎之图”就是山海经的古图[15],并认为古图秦朝时尚随《山海经》而见于世[16]。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认为《山海经》中“海外”“海内”诸经所指之图是禹鼎图,《大荒经》以下五篇则为汉所传图而“微与古异”,但两者均已失落。郝懿行引郭璞《山海经图赞》和陶渊明“流观山海图”句,认为至少到晋代经尚有图,但又认为二人所见已非古图[17]。至南朝张僧繇绘制、宋代舒雅重绘的十卷本《山海经图》,又已不同于郭、陶所见[18],是山海图的又一个版本系统,惟亦失传[19]。
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山海经图本,则来自于明朝的胡文焕本、蒋应镐本这两种。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7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代)出版的《怪奇鸟兽图卷》当中就有多幅根据明朝《山海经》图本而来的图像[8]。清代的山海经图以吴任臣图本最早,流传也最广。该书自叙其图是源自于舒雅的重绘本,不过仅取其“诡异”者144幅图,按灵祇、异域、兽族、羽禽、鳞介五类编排。后来毕沅、 郝懿行都以该图本为摹本。据马昌仪的研究,吴任臣图本有71幅图全部或大部采自胡文焕图本。另有汪绂本的图像407幅,则多是别出心裁之作,与其他明清山海经诸图本极少雷同[20]。十卷本《山海经图》及明清所见本,应是依据书中文字加以想像而绘图,但山海经可能是依照原始的山海图而形成文字[21]。
对于原始的山海图,杨慎等人认为是禹鼎(一作九鼎)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山海图为地图。王以中引毕沅“《五藏山经》34篇,古者土地之图”的说法,推测中国古代的地图是由山海图而演变;日本学者小川琢志在《〈山海经〉考》中认为西汉时期山海图与《山海经》并存,且山海图与欧洲中世纪所作的带有异人奇物的地图类似[22]。日本学者松田稔《山海经比较的研究》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图,在〈海外经〉与〈大荒经〉皆含有图画的叙述(即因图而作文),〈海外经〉是将一幅巨大的地图顺次序地“文章化”,而〈大荒经〉所根据之图画,很可能是一幅一幅单独的神人或动物等等的绘图[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昌仪,从现存的九种山海经图本中选出1000幅山海经图,配合山海经文字,著《古本山海经图说》,是当前研究山海经图的重要著作。
学术研究
[编辑]诗经传注
[编辑]清朝儒学学者、经学家廖平认为《山海经》是《诗经》的传注[23]。
神话学
[编辑]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的汇集,如文学家鲁迅认为:“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24]。”
茅盾、袁珂等人都从这观点看待《山海经》。茅盾表示:“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他反对把《山海经》当作实用地理书和小说看待。并著有《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一书,运用当时欧美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对山海经中的神话进行开创性研究。袁珂出版的《山海经校注》为如今研究山海经的必备注本,其专著《中国神话史》(1988)对《山海经》的神话做了详细描述。李丰楙的《山海经:神话的故乡》将山海经的神话内容整理为“山川宝藏”、“帝王世系”、“远方异国”及“神话信仰”,令人一目了然[25]。
按神话学者的认识,《山海经》中的女娲造人神话、射日奔月神话、黄帝蚩尤之战神话、西王母神话、桑蚕神话、夸父追日神话、精卫神话、刑天神话等,出自于上古华夏先民的口头创作,其不仅经由文字书面纪录下来,也长期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播,历经流变和二次创作的过程[26]。神话学对这些《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方向,除了以神话思维(亦即古人思考这世界的独特方式)来剖析其中的神怪内容,探究潜藏在叙事当中其深层结构的象征基础,也将《山海经》与《楚辞》、《逸周书》、《禹贡》诸书,或不同文化的神话,进行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发掘共通的母题和特点[25]。
近年来结合考古材料尤其是汉朝画像石进行《山海经》的神话研究成为热门项目,例如西王母、伏羲女娲、“操蛇神怪”的汉画像等。然而,考古材料文化解释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的主观揣测和比附,是此类研究的极大挑战[25]。
从民俗学观点来看,《山海经》也是了解先秦时代服佩、禁忌与祭祀习俗之宝贵资料[27]。民俗学家江绍原认为《山海经》具有“旅行指南”的性质,用以提示古人避开和应付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的神鬼精怪和毒恶生物[28]。伊藤清司将《山海经》作为民俗资料考察,把当中的神怪分为恶鬼和善神两大类,认为其确为古代圣贤传讲的辨别万物善恶之书,以应对危险的外部世界[25]。
道教学者李丰楙认为古人为了辨识神奸(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才会构成这种图像系谱。较古宝鼎上所刻的奇物图纹,这种形状凶恶的图像有神秘的镇压作用;后来持续流传,从巫者之手到方士、道士集团。在早期道经目录中,类似山海图的禹鼎记、白泽图等,主要的用途就是作为辟邪、防身的法术。而《山海经》的文字配合〈山海图〉的图像,就是源自这种辨识神奸的传统[29][页码请求]。
历史学
[编辑]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从原始朝向文明迈进的整体发展过程[30]。
将神话中的历史资料筛选出来的,以王国维用《山海经》印证甲骨文殷先王亥为最突出的例子[2]。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考出王亥、王恒系殷人的先公:“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祖”。杨树达、胡厚宣在考证卜辞之四方神名及四方风名时,均从《山海经》中发掘出所依据的资料[31][32]。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在研究、重建中国传说时代的文明史时,会运用 《山海经》 一类的史料作为佐证。
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认为《山海经》与〈天问〉中记载的神话故事是原初民族之世界观,保存了质朴心灵的古代史料,可从中找出“社会的背景,宗教的分素,文化的接触,初民的思想等等”,深具史料价值[33]。其所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即多援用山海经作为史料证据。称“《左传》之成分大体为晋楚鲁三国之语,而其立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甚不好。但《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中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显战国时羿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34]
治中国古代史,经学色彩浓厚的学者蒙文通引述“注疏图纬之成说”,对女娲、燧人氏、伏羲、神农、共工等神话人物不但加以运用,并且赋予特定的历史地位,将中国文化的源头定位为燧人氏[33]。蒙文通创立古史三系说,总结中国上古史为:宗孟子上合六经的“邹鲁”,宗韩非上合竹书纪年的“三晋”,以及宗屈原、庄子上合山海经的“楚”[35],他注意到《山海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主张该书可能是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36]。
提出“神话分化融合说”的杨宽作《中国上古史导论》将 《山海经》 用为材料之一,认为上古帝王世系不过是东西夷夏二系民族神话的层层分化融合[37];他自述其 “论古史神话” 之取向便是 “多据诸子及 《楚辞》、 《山海经》 诸书以为说”[38]。倡立“华夏、东夷与苗蛮”三集团说的徐旭生在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也大量采用《山海经》中材料,更指“从史料观点来看,为我国有最高价值书之一,而有此等价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2]。
地理学
[编辑]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如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30][39]。他以《山海经》来讨论战国以前古代人对“中国”边界的认识,认为那时大体上就已经形成东北为燕、辽东,北为赵、秦即沙漠南界,东为田齐即黄海沿岸,南方为楚即江南地方的空间[40]。
徐旭生指“〈五山经〉为古代遗留下相当可信之地理书。”“至海外经,海内,大荒各经,则几尽来自传闻,故可以今日之地理证明者颇少。”[41]不过,由于古今地名大多不同,再加上古人对方位道里勘定不甚精确,所以很多内容已失考[42]。
对《山海经》所记地理范围的讨论,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30]。
传统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据赫维人的研究),“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30]。持华夏说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持华夏说者,认为《山经》所载山川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正确性。偏远地区的资料采自传闻,就会比较失实[4]。
持局部小区说者,主张《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限于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30]。例如,王宁认为《山经》范围大体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于冀南、豫东和苏皖北部的地区其中所记的山川名称[43]。何幼琦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30]。持此说者,假定山海经中所记地名,与秦汉时同样地名,乃至于流传至今同样地名的所在地域无甚相干,而是地名外流的结果[43]。
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参见中国文化西来说)[44],后来有人进而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30]。上海大学文学教授沈海波批评世界圈说存在不少问题,缺乏可靠证据,有夸夸其谈之嫌[42]。
按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的考订,全部《山经》共载有447座山,其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实确切方位者为140座左右,占总数三分之一弱。这140座中的半数属于《中山经》,半数分属于南、西、北、东四经,而极不平衡。对今豫西、晋南、陕中地区的记载最为详确,离这地区越远,越疏略差谬[4]。
- 《南山经》东起今浙江舟山岛(漆吴山),西抵湖南沅水下游(柜山),南抵广东南海(《南次三经》诸水所注海)。可指实的最北一座山“浮玉山”,即今浙江东天目山。连带叙及的“具区”,即今太湖。
- 《西山经》东起山西陕西间的黄河,南达陕甘秦岭山脉,北抵今宁夏盐池西北(申首山)﹑陕西榆林东北(号山)一线,西南抵甘肃鸟鼠山以及青海湖(西海)、倒淌河(凄水),西北可能到达新疆阿尔金山(翼望山)。
- 《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漨﹑滑﹑彭水注于此),东抵河北中部(北次三经所见河水下游),南起山西中条山,北抵内蒙古阴山以北,北纬43°迤北一线(嚣水所注敦题山所临)。
- 《东山经》西起今山东泰山,东抵成山角(胡射山),北抵长山岛(𦍙山),南尽安徽濉河(䃌水)。
- 《中山经》自首山经至七山经,当今晋南豫西地。八山经为今鄂西地,十﹑十一山经为今豫西南地,十二山经为今湘北赣北地,皆在南﹑西﹑北﹑东西经之中。惟九山经地处西南,西起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崃山、崌山、岷山、章山),东至四川东部,并不居中。
相较于上述实证主义性质的地理学研究,叶舒宪则认为《山海经》按照南西北东中顺序展开的“五方空间结构”,并不是从现实的地理勘察活动中产生,而是某种理想化秩序理念的呈现,应定性为神话政治地理书。是山川地理志的现实描述与神话的交织,构建出“虚实相参”的空间图式,展现为“祭政合一”神权服务的宗教政治想像图景,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掌控的政治意图[45]。
自然科学
[编辑]另一种研究山海经的方式,是将山海经光怪陆离的记述,视为古人对实际观察到现象的精神崇拜,而试图用现代自然科学视野中的“自然现象”来加以解释。例如,羿(尧)射十日解释成当时世界性温热气候和局部地区干旱给人们带来的灾害,以及偶然出现的空气中晶体反射显示太阳幻影产生的多日假象。大量的怪物通过考古资料——如史前人壁画等的分析,解释为上古狩猎先民动物崇拜之衍化等等[30]。
这种研究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把烛龙解释为北极光。最早主张此说的是日本学者神田选吉。1983年,中国学者张明华提出《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烛龙是指北极极光[46],“人面蛇身,赤色,身长千里,钟山之神也。”,认为烛龙的形象和北极光一致[47]。
另外,从《山海经》的记载中,可探讨当时的科学知识。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我们可以从《山海经》中得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物质的知识[48]。龚胜生指出《山海经》记载了124种药物及其所治疗的30多种疾病,堪称中国最早的区域医学地理文献[49]。
清代学者陈逢衡则注意到《大荒经》中日月出入之山的记载,并认为这一记载与观察日月行度以确定晷度的习俗有关[50]。科技史学者吕子方同意此一说法,认为“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太阳所出之山六座,《大荒西经》记日入之山也是六座。这是观察太阳出入的地位,以便安排耕种日程,也是确定季节最原始的方法。如果不这样去理解,那又怎么解释呢[51]?”刘宗迪主张《荒经》有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反映了上古历法的阴阳合历制度,是原始的天文学测量方法[52]。
评价
[编辑]-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山海经疑诘〉以评价:“予读《山海经》,每卷首标之曰:‘大禹制,郭氏传’,则此经当谓夏禹所著矣;然予疑非禹制。何者?传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论语》曰:‘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盖恶之也。’孔子修《春秋》,虽直笔之书,以鲁为父母邦,凡大恶则皆讳避不书。若《山海经》果是禹制,当讳父之大耻。观〈东北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是禹父,不宜斥书此事,若以为实事不得不书,则不甚言‘窃’,而云‘取’帝之壤,亦不蔽于义也。按〈献经表〉云:‘昔洪水洋溢,鲧既无功,高使禹继之。伯益与伯翳驱禽兽、别水土,纪其珍怪。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贤圣之遗事。’据此则疑伯益所著,然其序,则云禹别九州,物无遁形,因著《山海经》云云;此二说亦不同,是皆所惑者。又有一惑焉,《尚书》曰:‘高殛鲧于羽山,盖以鲧理水,绩用不成故也。’此经云:帝殛鲧于羽郊,所谓帝者,上帝也。鲧虽窃帝壤,苟能堙洪水?则于高为有功,于帝为有罪,高不宜诛,而帝独诛矣。若为帝所诛,又不当为高所殛,若为高所殛,则其不窃帝壤堙洪水明矣。上帝其何名而杀鲧耶?此二说亦不同。安所从耶?在醇儒,当以《尚书》为正,而以《山海经》为荒怪之说矣。然既曰禹制,禹之说,可谓怪乎?待后之明智君子有以辨之耳。”
译本
[编辑]-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译者: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l),Penguin Classics,2000年,ISBN 0-14-044719-9
- Chan-Hai-King V1: Antique Geographie Chinoise (1891),译者:De Rosny, Leon,Kessinger Pub,2009年,ISBN 978-1-104-07985-7
图片
[编辑]-
九尾狐(清人所绘)
衍生作品
[编辑]地图
[编辑]文学
[编辑]绘画
[编辑]音乐
[编辑]电影
[编辑]- 捉妖记
- 大鱼海棠
- 捉妖记2
-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英国、美国;经中神兽“驺虞”以神奇动物形式出现)
- 尚气与十环传奇(美国;经中山神“帝江”以吉祥物形式出现,片中被英国演员崔佛·史莱特利命名为莫里斯)
- 山海经之小人国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电视剧
[编辑]电视纪录片
[编辑]动漫
[编辑]- 小太极
- 精卫填海
- 山海奇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14年;CCTV新科动漫频道首播)
- 非人哉
- 山海逆战
- 不白吃话山海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山海经之兵主奇魂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游戏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陈连山. 《山海經》「巫書說」批判——重申《山海經》為原始地理志. 民间文化论坛. 2010, (1): 12-19. ISSN 1008-7214. doi:10.16814/j.cnki.1008-7214.2010.01.002. CNKI WHLT201001002
 .
.
- ^ 2.0 2.1 2.2 2.3 2.4 舒铁. 学术转型视野下的《山海经》与民国古史研究——以王国维王亥考证为中心. 史林. 2017, 6. ISSN 1007-1873. CNKI LWBI201706017. NSSD 674200924
 .
.
- ^ 刘宗迪. 《山海經》背後的秘密竟然是……. 凤凰读书. 2017-08-31 [2017-10-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汉代学者刘歆、王充相信此书是大禹和伯益在治理九州、周流天下时记载山川风土的地理风俗志;东晋学者郭璞认为此书是荟萃方外珍奇、阐发要道妙论的博物之书;朱熹称此书是依托《楚辞·天问》凑合之作,又称此书与《天问》一样,是摹写图画而成;明代学者胡应麟视此书为古今语怪之祖,纯为战国好奇之士搜采异闻诡物编造而成;明代学者杨慎说此书记载的是禹贡九鼎上那些魑魅魍魉的图像。到了现代,西学输入,学者眼界大开,对《山海经》的认识也异彩纷呈、众声喧哗。鲁迅说它是古之巫书,记载的是古代巫师祭神厌鬼的方术仪典;茅盾、袁珂说它是远古神话,寄托了华夏先民丰富而奇丽的想像。
- ^ 4.0 4.1 4.2 4.3 谭其骧. 山海經. 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全书内容庞杂﹐自然方面的山﹑川﹑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象、人文方面的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疾病医药﹐以及古帝王世系﹑葬地和发明制作﹐无所不包。《山经》所载山川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正确性。部分偏远地区资料采自传闻﹐无从核实﹐离地理实际就相当远。记述方式是先按大方位分成5区﹐即以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命名﹔次将每区的山分为若干行列﹔然后每一列从首山曰某山叙起﹐依次叙又某向若干里曰某山﹔山下叙某水出焉﹐某向流注于某水或泽或海﹐或无水。
- ^ 《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杜佑认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胡应麟则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2页)
- ^ 6.0 6.1 6.2 6.3 6.4 黄春贵. 山海經探微 (PDF). 教学与研究. 1979, (1) [2017-10-31]. ISSN 1016-3026. doi:10.6250/TR.1979.1.5.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11-07).
-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载: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记事之词大异……意为先有斯图,撰者因而记之,故其文义应尔。”
- ^ 8.0 8.1 8.2 马昌仪. 山海經古圖與中國以圖敘事傳統. 邓启耀 (编). 《视觉表达:2002》. 2003: 41-135 [2017-10-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9.0 9.1 9.2 柳倩月. 清代學統中的《山海經》序文與「神話歷史」觀之學術邏輯. 中原文化研究. 2017, 5 (6): 92-97 [2019-02-16]. ISSN 2095-5669. doi:10.16600/j.cnki.41-1426/c.2017.06.013. CNKI ZYWH201706014. NSSD 673667992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17) –通过中国作家网.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17) –通过中国作家网.
- ^ 刘歆,〈上山海经表〉,《全汉文》卷四十
- ^ 赵晔《吴越春秋》:“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媒。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轰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日山海经。”
- ^ 陈槃《论早期谶纬与邹衍书的关系》,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二十、上
- ^ 13.0 13.1 13.2 黄正谦. 論《山海經》與中西神話比較的視角——《山海經》導讀.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文献通考》卷204
- ^ 杨慎《山海经后序》:“则九鼎之图也,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谓之曰山海图。”
- ^ 杨慎《山海经后序》:“至秦而九鼎亡,独图与经存。”
- ^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郭注此经而云:‘图亦作牛形’,又云:‘在畏兽画中’;陶征士读是经诗亦云:‘流观山海图’:是晋代此经尚有图也……然郭所见图,即已非古,古图当有山川道里。今考郭所标出,但有畏兽仙人,而于山川脉络,即不能案图会意,是知郭亦未见古图也。”
- ^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中兴书目》云:‘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重绘为十卷,每卷中先类所画名,凡二百四十七种,是其图画已异郭、陶所见。’”
- ^ 毕沅《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又图十卷,梁张僧繇画,亦亡。”
- ^ 马昌仪. 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 (PDF). 西北民族研究. 2005, (3) [2019-02-16]. ISSN 1001-5558.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05.03.004. CNKI SAGA200503010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17).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17).
- ^ 王以中. 山海經圖與職貢圖. 禹贡. 1934年, 1 (3): 8.
除毕沅所谓汉所传大荒经图及郭璞等所见图,或略存古图经之遗意外,此后大抵皆因文字以绘图,与原始《山海经》之因图像以注文字者,适如反客为主。
- ^ 马昌仪. 古本山海經圖說 (PDF).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4.
- ^ 《〈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
- ^ 《山海經》性質特點.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25.0 25.1 25.2 25.3 陈帅. 《山海經》神話研究綜述. 学理论. 2013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张佳颖; 张步天. 《山海經》神話群系"的傳承流變.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2006, (4): 21-24,10. ISSN 1008-3421. doi:10.3969/j.issn.1008-3421.2006.04.005. CNKI FJFQ200604004
 . WFdata:periodical/fjsdfqfxxb200604005.
. WFdata:periodical/fjsdfqfxxb200604005.
- ^ 张紫晨. 山海經的民俗學價值 (PDF). 思想战线. 1984, (4): 78-85 [2017-11-02]. ISSN 1001-778X. CNKI SXZX198404013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11-07).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11-07).
- ^ 李乔. 江紹原:古代旅人的迷信. 新华网. 2009-02-07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7-04).
- ^ 李丰楙. 山海經圖鑑. 大块文化. 2017. ISBN 978-986-213-817-5.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张步天. 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顧. 青海师专学报. 1998, (3): 56-59 [2017-11-02]. ISSN 1007-0117. CNKI QHSX199803011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17).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17).
- ^ 张京华. 古史研究的三條途徑 ─ 以現代學者對「絕地天通」一語的闡釋為中心 (PDF). 汉学研究通讯. 2007, 26 (2) [2017-11-02]. ISSN 0253-287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11-07).
近代以来从史学方向研究《山海经》的最重要成果当属王国维1917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该文取《山海经》〈大荒东经〉与殷商卜辞中所见先公“王亥”之名互相印证,证明《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世本》、《吕氏春秋》〈勿躬〉、《楚辞》〈天问〉、《初学记》、《太平御览》所载“振”、“振”、“垓”、“核”、“冰”、“该”、“胲”、“鲧”等字均为讹变,诸书中惟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所记作“亥”字为是。顾颉刚在1955年的一则读书笔记中说道:“《山海经》经司马迁与谯周打击之后,颇不为当时学者所信,几于失传。幸有汲冢竹书发现,而其中《纪年》、《穆传》两种大可与《山海经》相证,刺戟郭璞起而作注,注中辄引二书,遂使《山经》、《穆传》并存于世,《纪年》虽亡,亦可由是辑出若干。此地下遗物之发现竟救活了一部《山海经》,可谓幸矣。至于今日,以甲骨文字之发现,王国维取以证王亥,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而《山经》所记又得证实一部分。”表面看来顾先生的见解与王国维相近,实际上仍有绝大不同。因王国维相信“地下之新材料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顾颉刚则相信“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王国维的研究期于证明《山海经》中保存信史资料,而顾颉刚则始终坚持其为神话书,至多只是书中的神话出现得较早而已。
- ^ 王晖. 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蕴义及原型演变. 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11-02]. CNKI EGYF20040000104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31).
- ^ 33.0 33.1 张凯. 經史嬗遞與重建中華文明體系之路徑 ——以傅斯年與蒙文通學術分合為中心.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44 (2): 26-40 [2017-11-02]. ISSN 1008-942X.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3.09.061. CNKI ZJDX201402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29).
- ^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1933年).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1-09).
- ^ 黄正谦. 山海經【新視野經典文庫】. 新视野中华经典文库: 历史地理系列.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4: 60-? [2017-11-02]. ISBN 978-988-8290-47-5.
- ^ 刘复生. 通觀明變,百川競發——讀《蒙文通文集》兼論蒙文通先生的史學成就.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104-109 [2017-11-03]. ISSN 1006-0766. doi:10.3969/j.issn.1006-0766.2004.06.017. CNKI SCDZ200406018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赵惠瑜. 楊寬的中國神話研究 (硕士论文).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 2009. hdl:11296/36fw72.
- ^ 杨宽. 上呂師誠之書. 1940.
- ^ 刘正. 四重證據說視野下的京都考證學派. [2017-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他(小川琢治)利用古今各种传本的比较,开始了《山海经》错简和佚文的研究。最后又把和《尚书·禹贡》进行相互引证,他得出结论说:此经名实为名山道理记,即山川祭祀之指南记,既如毕沅所言。而其记载,以洛阳为中心,西为泾渭诸水之流域,即雍州之东部诸山。北自汾水中流以南,即冀州南部诸山。最为详密,殊于洛阳近旁,伊洛之间,及豫州诸山,极为精细。然于东方东南方诸山,能考定者极少,至于北方更少。观其所说山名之祭典,于五岳无特设之盛腆泰山与东岳无区别,唯记嵩山用太牢。凑合此等诸点而考之,则五藏山经之文,其在东州都洛阳时所者乎?从其志山岳及地名之得考定者,记事颇能正确者而推,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者与?……小川琢治以他和王国维先生对《山海经》的史料考证为根据,反驳桑原隲蔵的质疑。桑原隲蔵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他看重的是第一重证据。而小川琢治则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信性。
- ^ 葛兆光.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PDF).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2018 [2017-11-07]. ISBN 978-988-237-014-2.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09-30).
- ^ 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附录三》(上海市〆上海,1990),页 355-356
- ^ 42.0 42.1 沈海波. 怎樣讀《山海經》.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25).
- ^ 43.0 43.1 王宁. 《五藏山經》記述的地域及作者新探. 管子学刊. 2000, (3): 77-84 [2017-11-02]. ISSN 1002-3828. doi:10.19321/j.cnki.gzxk.2000.03.015. CNKI GZXK200003015. NSSD 12481855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蔡玫姿. 域外文化的想像與詮釋 —— 蘇雪林學術研究方法探源 (PDF). 成大中文学报. 2007, (18): 143-175 [2017-11-02]. ISSN 1817-0021. doi:10.29907/JRTR.200710.000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07-08).
- ^ 唐启翠; 胡滔雄. 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综述.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9 (2): 19–23. ISSN 1673-1395. doi:10.3969/j.issn.1673-1395.2006.02.003. CNKI JZSZ200602003
 . WFdata:periodical/jzsfxyxb-shkxb200602003.
. WFdata:periodical/jzsfxyxb-shkxb200602003.
- ^ 《山海经新探》(成都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页308-314。后收录《学林漫录》第8集
- ^ 蔡哲茂. 燭龍神話的研究——以現代天文學來印證. 1994-03 [2023-08-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8-09) (中文).
- ^ 李约瑟,《中国之科技文明》第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页 54~55
- ^ 龚胜生; 罗碧波. 《山海经》的医学地理学价值 (PDF).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46 (3): 351–357 [2019-02-16]. ISSN 1000-1190. doi:10.3969/j.issn.1000-1190.2012.03.023. CNKI HZSZ201203022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17).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17).
- ^ 《山海经汇说·山海经多记日月行次》云:“《大荒东经》言日月所出者六,盖各于一山测量其所出入之度数以定其行次也。”“《大荒西经》言日月所入者七,盖各山皆设有官属,以记其行次,然后汇而录之,以合其晷度,如今时各有节气不同也。”
- ^ 于奕华. 《山海經》以山紀日月出入功能考略——論六十四卦畫古歷的基礎.
- ^ 刘宗迪. 《山海經-大荒經》與《尚書-堯典》的對比研究. 民族艺术. 2002, (3): 58-75 [2017-11-02]. ISSN 1003-2568. CNKI MZYS200203008
 . NSSD 12300865
. NSSD 12300865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延伸阅读
[编辑][在维基数据编辑]
 在维基文库阅读本作品原文(
在维基文库阅读本作品原文( 在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分类)
在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分类) 《山海经 (四库全书本)》
《山海经 (四库全书本)》 《山海经 (四部丛刊本)》
《山海经 (四部丛刊本)》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山经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山经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研究书目
[编辑]- 杨锡彭《新译山海经》,三民书局,2009年
- 陈成《山海经译注》,上海古籍,2012年
- 黄正谦《山海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华书局,2014年
- 袁珂《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北京联合出版,2014年
- 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ISBN 7-80603-521-4;
最新版本为: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ISBN 978-7-5633-6397-1,收图1500幅,采选的版本达16种。 - 徐客《图解山海经:解读中国神话之源,认识上古山川地理和奇兽异族》,西北国际,2014年
- 陈丝雨,孙见坤《山海经:怪兽与它们的产地东方版》,华滋出版,2016年
- 李丰楙编审《山海经图鉴》,大块文化 ,2017年
-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
- 李丰楙《山海经:神话的故乡》,时报出版,2012年
- 陈连山 《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外部链接
[编辑]- 《山海经》原文及译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山海经》全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山海経动物记 表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文学的神话仙乡--山海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山海经探微
- 《山海经》与谶纬中的远国异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楚辞》《山海经》神话趋同的文化学意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山海经》史料比较研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从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看今本中存在的问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